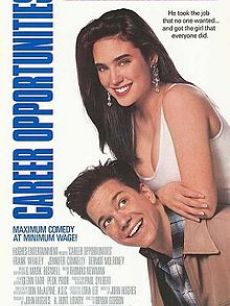- 三三云1
- HD

影子
- 主演:
- 王凡秋岑,金千寻,何莲
- 备注:
- HD
- 类型:
- 微电影 剧情
- 导演:
- 何莲
- 年代:
- 2014
- 地区:
- 内地
- 更新:
- 2024-03-31 14:52
- 简介:
- 备案号:1904073150402268 《影》是一部向全世界女性导演致敬的微电影。这部电影属于青少年题材。这是一个关于“救援”的故事。有自救和他人帮助。正如片名所说:《坚强的自救》,这部电影在追求命运和梦想的过程中,突出了“自救”的主题。贵州第八代华人导演代表——女.....详细
1989年是美国电影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年。
这一年,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独立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在圣丹斯电影节一鸣惊人,四个月后,这部处女作从戛纳捧回了金棕榈大奖,影片与圣丹斯相互成就,助推了90年代异军突起的美国独立电影浪潮。
同年,约翰·卡萨维蒂病情加重的消息传开,圣丹斯和鹿特丹电影节分别举办回顾展向这位“美国独立电影教父”致敬,影展结束不久后的2月3日,卡萨维蒂病逝于洛杉矶,终年59岁。
卡萨维蒂的首部长片《影子》被公认为美国独立电影的先驱之作,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卡萨维蒂创办的演员工作坊的一次表演训练:一个非裔美国女孩和一个白人男孩约会,随着交往的深入,他厌恶地发现女孩的哥哥是个黑人。卡萨维蒂仅仅勾勒出故事的框架,而不填充情节,随着演员的即兴表演,影片完全围绕人物本身展开,所有角色都由工作坊的学员出演。1957年,靠着一台从雪莉·克拉克那儿借来的16毫米手持摄影机,卡萨维蒂在纽约街头和自己的公寓完成了电影的拍摄,中途几度因为技术和演员问题而停滞。
1958年秋天,《影子》在纽约的巴黎电影院举办了非公开的首场放映,然而观众反响并不令卡萨维蒂满意。他决定修改电影,在1959年对其中大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拍和重新剪辑。然而这第二个版本依旧反响平平,当时观看了放映的乔纳斯·梅卡斯甚至专门在《村声》撰文,指出这一版“只不过是又一部好莱坞电影”,远远不如原版那般先锋。
尽管在本土遭到冷遇,《影子》却在次年得到了英国《视与听》杂志的良好口碑,在英国电影学院奖上大放异彩,并在威尼斯电影节拿到了一个平行单元的奖项。载誉而归的《影子》恰好遇上了正处在作者论熏陶中的美国电影界,终于重振旗鼓,正式开启了卡萨维蒂的导演事业。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影子》最初的版本从此就如同人间蒸发一样,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放映,人们看到的都是1959年重拍的第二个版本。三十年后,波士顿大学的教授雷·卡尼在与卡萨维蒂的对话中,得知了第一个版本的下落:它很可能被捐赠给了某所高校。卡萨维蒂去世后,卡尼开始专注于寻找《影子》的初版拷贝,然而,随着搜索的推进,卡萨维蒂生前给出的线索都成了死胡同,这个神秘的《影子》似乎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雷·卡尼也一度想放弃搜索,他试着换一个思路,从参与过初版《影子》的演职人员和第一批观众口中,还原出它的模样,在此期间,他为英国电影协会写作了《影子》一书,后又将两个版本的对比研究补充进去。
就在卡尼的专著出版后,新的线索出现了,一个女人称自己收废品的父亲从地铁站举办的丢失物品特卖会里买到了第一版的《影子》。但是由于年代久远,父亲也已去世,找回拷贝的几率微乎其微。然而就在连卡尼都不抱希望的时候,女人的亲属在阁楼中找到了积满灰尘的胶片盒——其中正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影子》初版拷贝。
十七年时光只为搜寻一部电影,初版《影子》的寻回过程就如同它的制作和观众接受过程一样波折。雷·卡尼本人于2004年撰写了这篇文章,以轻松生动的口吻回忆了这场漫长、传奇般的发现之旅,阅读过程中仿佛我们也亲自经历了每一次惊喜、失望和“命运的玩笑”。
Chasing Cassavetes’ Shadows
“逐影”卡萨维蒂
作者:Ray Carney
翻译:麻友安
在《公民凯恩》的开场处,查尔斯·福斯特留下遗言“玫瑰花蕾”,一位记者四处搜集线索,从这仅有的两个音节中拼凑出了他的一生。
假若人生也如电影一般简单就好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约翰·卡萨维蒂离世前几年,我与他进行过一系列“玫瑰花蕾”式的对话。这位美国独立电影人向我讲述了他的生活,以及他此前从未透露过的作品。我们的讨论涵盖大量领域,但我问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便是他的电影不同的版本都有着怎样的命运。
卡萨维蒂的大多数作品都独立于制片厂制度之外,由他本人筹集经费(利用他给其他导演做演员赚来的钱),因此他得以脱离那些限制住好莱坞电影人的条条框框。他想拍多久就拍多久,想剪多久就剪多久,假如他乐意,大可按照他的想法重拍或者重剪。一言以蔽之,卡萨维蒂拍电影就如同诗人写诗,画家作画。
相应的结果就是,在他创作的各个阶段中,大部分的作品包括《面孔》、《夫君》、《受影响的女人》、《谋杀地下老板》都存在着大相径庭的各式版本,人物不同,场景不同,片长也不同。
我们谈论最多的电影就是《影子》。它是卡萨维蒂的第一部长片,被公认为美国独立电影运动的开端,也曾有过一段争论不休的历史。本片实际上拍了两遍,最初的版本1957年完成,1958年秋天在纽约的巴黎电影院向受邀观众展映。但由于对反响不满意,卡萨维蒂在1959年对影片的大部分内容进行了重拍,原版拷贝中约有一半的内容都被新素材替换掉了。1959年晚些时候,所谓的“第二版”《影子》首映。
有件事让《影子》的故事变得格外有趣,一些看过两个版本的影评人和观众,坚信卡萨维蒂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乔纳斯·梅卡斯发表在1960年1月27日那期《村声》杂志上的电影日志专栏写道:“我毫不怀疑,尽管第二版《影子》时而让我受到启发,但它也只不过是又一部好莱坞电影,然而第一个版本却是这十年来最前沿最有突破性的美国电影。假如它能被正确地理解和展示,便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整个美国独立电影的基调、主题和风格。”
在文章结尾,梅卡斯希望卡萨维蒂恢复理智,压下第二个版本,放出第一个版本,但现实并非如此。卡萨维蒂收回了早前的拷贝,并且拒绝让它再次放映。从那时起,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版《影子》就是被重新剪辑过的第二版,这也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版本。
当我向卡萨维蒂问起第一版拷贝的下落时,他怀疑已经不见踪影。考虑到他在50年代的简朴作风,这个版本幸存的可能性就显得更加渺茫。他告诉我,第一版《影子》只有一个16毫米胶片拷贝。他没有足够的钱做副本或备份,原先的负片也被用去剪第二个版本了。
他给我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他依稀记得把第一版捐给了一所电影院校。之后乔纳斯·梅卡斯告诉我,他曾经听卡萨维蒂更确切地提起过一次,捐给了“一所中西部的学校”。
我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我联系了每一所位于中西部的学校,首先就是卡萨维蒂的妻子吉娜·罗兰兹的母校威斯康星大学,看似最有可能。为了保证不落下任何线索,我还去追踪了影片制作时期学校电影项目的相关人员,大概是25到30年前的事了。我收获了很多精彩的对话,交到了新朋友,但却空手而归。
1989年卡萨维蒂逝世前后,我扩大了搜索。我联系了每一个主要的美国电影资料馆、博物馆和高校的电影项目,想知道拷贝是否可能深藏于他们的馆藏之中。毕竟,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片名是一样的,或许他们有第一个版本而并未发觉。我开始在自己组织和主管的电影活动中公开发表声明,我拜托我的影评人朋友、电影制作人和普通人们广而告之。90年代中期我建立起一个网站,在上面发布公告。朋友们都跟我开玩笑,称“追逐《影子》的影子”已经成为了一种狂热。
在此后的十年里,我收到的建议和可供追踪的线索层出不穷。我曾亲自与数百人交流,通电话,随后是电子邮件。我找到了参加过最早几次放映的观众,记录下他们对于第一版本内容的描述。我和那些认为对它的下落有所了解的人一一交谈。有那么些日子,它眼看着就要触手可及了,只要我能通过某个人认识的人认识的人联系上“那个人”。然而“那个人”总是和我擦肩而过。我数次铩羽而归,飞到陌生的城市会见一位收藏家,被引导相信他拥有第一版拷贝。当然了,每一次都会发现那其实是第二版。
我还没有丧失幽默感,我那些乐在其中的朋友也是。关于第一个版本的内容,很多陈述之间都是相互矛盾的,包括卡萨维蒂本人的,以至于我开玩笑道,这场搜索持续得越久,我了解的就越少。
刚开始的时候一切可比现在清楚多了。我既教电影也教文学,有一天在一次亨利·詹姆斯的讨论会上,我正谈到《阿斯本文稿》和《地毯上的图案》——两篇滑稽故事,关于无尽、无意义的疯狂的学术搜索,最后都无疾而终,这时我开始狂笑不止,不得不暂停讨论,向学生们解释道我突然从詹姆斯的人物中意识到了自己的那份学者狂热。我是疯了吗?
命运曾对我耍了好几次花招。比如,当我在国会图书馆寻找《影子》的拷贝时,我意外发现了未被归类识别的《面孔》较长版本。很有意思,很有价值,但对不起,不是我要找的。
我不能说自己没有过挫败感。90年代中期的一段日子里,我把搜索拷贝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决定换一种方法。假如我找不到第一版拷贝的实物,那么我可以在想象中把它重新建构出来,通过演员、剧组成员、观众的回忆,也通过对第二个版本的研究,第二版中有约莫30分钟的内容是来自第一版的。我重新采访了演职人员,收集他们关于第一版的记忆,然后逐个镜头地研究第二个版本,找出提示情节的线索以区分1957和1959拍摄的不同素材。这就是学者们所谓的利用“内在证据”去研究一部作品的修订版本。
这项研究几乎全部都得在电影院放映厅里展开,因为普通的视频图像无法展现出我需要用于推论的那种细节。我呼朋唤友,一边抱怨一边拉着他们去电影院看35毫米胶片放映,发给他们做笔记用的板子,我们一起坐在前排,互相耳语,记下两个连续的镜头里演员的袜子或者头发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下了投在地上的阴影的长度,以确定拍摄的时间,还有树叶的大小和公园里花朵盛开的程度,用以确定月份。我们记下背景中车辆的型号,可见的电影和戏剧的名字。这些只是原材料,实验数据,真正的乐趣在于把它们联系起来,通过这样蜘蛛网般的交叉纠缠来重构起完整的第一版。背景中影院门口一部电影的片名,能让我们追溯回女演员这个发型对应的日期,然后便可借此确定另一个场景中男演员戴过的围巾是出现在哪一天……以下省略三四个中间步骤,最后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和此前所有场景都完全不同的场景,绝对就是1957年三月的一天下午拍摄的,晚些时候还下了一场大雨。
我们经历了许多场放映和数年的线索记录。《影子》是一张巨大的拼图,有着上千块遗失的碎片,随着我和朋友一点一点拼起碎片,更大的版图浮现出来,展示着两个不同时期所拍摄的内容。这也许不是我做过的最高深的学术研究,但它一定是最好玩的——有点像一边玩棋盘问答游戏,一边做着《时代周刊》的填字游戏,同时还将魔方扭成每面同色。填字的横排引导我完成竖列,魔方的边缘提醒我界线所在,而电影中的海报让我找到了袜子、围巾和发型的线索。《影子》成为了我个人的《死海古卷》。解码罗塞塔石和B类线形文字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何其有趣。
最终我出版了两本总结性的书籍:第一本是关于本片的专著,属于英国电影协会的经典电影系列丛书,第二本是我在个人网站上出售的这本专著的扩写增订版。(在英国电影协会那本书出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继续参加放映记录笔记,就是停不下来。)
接着,两年前的某一天,就在我的书出版了一段时间后,一个朋友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曾经告诉过他关于搜寻《影子》的事情,他说他遇见了一个可能知情的女人。当我终于联系上她时,又是典型的“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的局面。好消息是她确认了这个片名听起来很耳熟,她父亲是一个混迹于曼哈顿二手店的“废品商人”,他补充库存的一个途径就是参加纽约地铁系统举办的“失物招领”售卖会。那里有被人丢失的雨伞、手套、眼镜、帽子、钢笔等等太多东西,以至于运输管理局每年都要拍卖这些无人认领的物品。虽然一块不错的手表可能卖到十块二十块美元,但是其它都只要一两块钱“一箱”——可能装着几十上百个雨伞、手套或者帽子。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年(具体日期无法确定),在她父亲买走的箱子里装了一个纤维板做的胶卷盒。他回到家,打开盒子,看到了其中一卷胶片的片头写着“影子”(至少他女儿记得是这么说的),但由于他从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还开玩笑道可惜不是一部“黄片”。
在这件事上,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地铁可不是第一版应该出现的地方。不仅不符合卡萨维蒂的说法,这个场景也听上去很不真实。假如全世界唯一一个拷贝被落在了地铁车厢里,为什么失主第二天没有去找回?它是第一个版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卡萨维蒂成为一个知名导演后,第二个版本制作发行了几百个拷贝。鉴于那位女儿不清楚拿到拷贝的日期,那么更有可能是第二版,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学校或者艺术影院放映过的拷贝之一。
更坏的消息是这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大约三四十年前。我和她最早的一次对话中,她强调道即便假设她的记忆是正确的,那个拷贝也几乎不可能还存在。废品店很久以前就关门了,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家庭成员都不再在纽约生活,儿女们都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搬去了别的城市。很多年前,商店的货品要么被卖掉了,要么就被清理了。“影子”只是来自一则好笑的家庭故事中依稀记得的词汇。这个女人不在乎拷贝的存亡,当我向她请求时她甚至并不想去寻找。她告诉我完全不知道从哪找起。
我得花上将近两年时间“礼貌地叨扰”,她才能想出来一点东西,但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也循例每隔几周提醒她向其他家庭成员打听拷贝的下落,但我已经私下里把这条线索当成又一个此路不通的死胡同排除掉了。我重新开始在卡萨维蒂相关的活动上发表公告,在我的网站以及别处发布问询。
这就是为什么当胶片终于被找到,从废品商儿女在弗罗里达的房子的阁楼里翻出来,运送到我家,到我手上时,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快递员把包裹放下后,我看了一眼盒子里的胶片,确认片头写了“影子”两个字,但我做完这些之后,就把胶片放回了盒子,扣好胶片包装箱,继续做我的教务功课去了。我确信,这绝不会是我要找的那个的拷贝。
几个小时后,我从第一本胶片里拉出四到五英尺来,对着台灯的光线端详,这时,我的冷漠骤然变成兴奋,随即又转为恐慌。我只能看出一个人影行走在街头,但这已经足够。因为第二版的开头是一场群戏。
十秒钟之内,我从原先的漫不经心,变得不敢去触碰它,生怕留下指纹。我家里有放映室,但我一点都不敢放映这些胶片,尽管我如饥似渴地想要看到比这开场三秒钟更多的内容。(你可以想象这需要多强的自制力。)假如这真就是失传已久的第一版《影子》,而我的放映机出故障把它碾成碎片那就完了。哪怕只是胶片在放映机中经过时留下一点点微小的刮擦,那也是我的自私和失职。我应当把它留给后世。我小心翼翼地把箱子封装好,第二天预约了一家专业的胶片转制工作室为它做一版高清视频拷贝——这样一来原版就再也不需要经过任何放映机了。时间上的推迟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要等上一周才轮到我的预约,这一周我忽然焦虑难眠,充满着所有收藏家都了解的那种完全非理性的恐惧,害怕在这期间会冒出一场大火烧毁我的房子,我不断掂量着咖啡桌上的包装箱,告诉自己胶片还在里面。在我终于得见搜寻十七年的电影之前,我经历了这样的一周。
这些胶片在每一个层面都远远超出我的期待。内容上,它多出了30多分钟后一个版本没有的场景。关于卡萨维蒂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有点像发掘了五到十幅毕加索的早期作品。从物质层面来看,尽管片基历经五十年的贮藏已经萎缩易碎,但其上的感光乳剂状态极佳。可别忘了,这可不像我们在影院看到的电影,或者我看过的第二版《影子》,它不是副本,未经放大,并且只被放映过四到五次,之后卡萨维蒂就将它收回。作为胶片,它洁净如初,极尽锐利和清晰。它不仅直接从卡萨维蒂1957年拍摄的原始负片冲印过来,实际上,它是崭新的,没有磨损或划痕,因为它再也没有被观看过。就两个版本共有的场景而言,这第一版的画面质量甚至比UCLA最新修复过的第二版还要好得多。
或许有人会问,乔纳斯·梅卡斯说得到底是对是错,但这已经不再重要了。每一个版本的《影子》都是一件独立的艺术品。第一版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有机会走进幕后,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艺术史学家们用X光扫描伦勃朗的画作,只为一瞥他变化的意图。批评家们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四开本和第一对开本之间的差异。但之于电影,几乎从未有过类似的实践。这就是第一版《影子》的价值所在,它让我们窥见卡萨维蒂的创作过程——如同他拍摄剪辑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时,我们就站在他身后。我们看到他改变自己对电影和角色的理解,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的变动——他增加场景,删除场景,加入对话,配上音乐,在重拍和重剪时不断变换位置,提供了几乎前所未有的观察视角,让我们走近这位过去五十年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窥见他的心灵和思想。
找到第一版的几率之渺茫,依然令我震惊——不仅因为在这样一个意料之外的地方找到全世界唯一一个拷贝,还因为时机。废品商的子女们都已经年过半百,等到他们去世时,装着胶片的纸箱子必定会被当做垃圾丢掉。(其中一位已经去世了。)我的朋友们曾经开玩笑,说我这是在草垛子里找一根针,但当我找到的时候才意识到,真实的情况甚至比这个比喻还要极端。“草垛”将不久于人世,不出十五年它就将被烧成灰烬。假如胶片存放在资料馆或者博物馆里,它大可在那里再等上千年,直到有人发现,然而作为一个一文不值的留在阁楼角落积灰的物件,它不可能再从下一代的大扫除中幸存了。但是当我在寻找时,并未察觉时间紧迫,找到它后我才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永恒之中最后的一次机会。
至于它为什么会被落在地铁上,谁都可以来猜一猜。我自己的理论(基于我认识的参加过先前放映的人士,不过我可不敢指名道姓)是和第一版有关系的人之一,拎着箱子从最后一次放映的地方回来,这时一位迷人的金发女郎上了车。剩下的我留给你们去想象。谢天谢地,幸亏有金发女郎,和废品商人。
原文: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04/feb/21/features
作者简介:
雷·卡尼是美国独立电影和艺术电影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任教于波士顿大学电影电视系,他既是约翰·卡萨维蒂的生前好友,也是研究其电影及生涯的专家,著有《美国幻梦:约翰·卡萨维蒂的电影和美国经验》(1985)、《卡萨维蒂电影:实用主义,现代主义及电影》(1994)、访谈传记《卡萨维蒂论卡萨维蒂》(2001),英国电影协会经典电影丛书《影子》(2001),以及《欲望的语言:卡尔·德莱叶的电影》(1989)等书,曾设立卡萨维蒂纪念网站。
附图:
电影胶片包装箱,箱子里放置胶片盒,文中废品商人买到的第一版《影子》应该就是装在这样的箱子里。